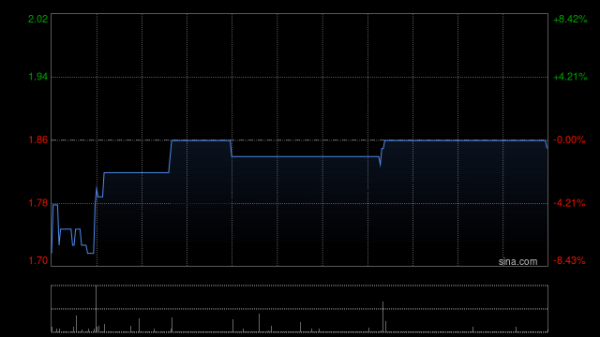邵毅平著
第一讲 文学作品的空间解读——从《江南》出发
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《江南》,在一般人的印象中,应该是一个很“小儿科”的文本。其实这首汉乐府民歌却一点都不简单,其中隐藏着中国文化、中华文明的重要密码。这一讲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,如何从一个貌似“简单”的文学经典文本中,发现其中所隐藏的重要的文化、文明密码。
一 “采莲”的发端
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
展开剩余84%这首题为《江南》的汉乐府民歌,近乎儿歌般简单,却是汉代诗歌里的一朵奇葩,在文学史上可谓影响深远。汉乐府多为北方民歌,这是仅见的江南民歌。它最初载于《宋书·乐志》,后收入《乐府诗集》,属《相和歌辞·相和曲》。《宋书·乐志一》云:“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,并汉世街陌谣讴,《江南可采莲》……之属是也。”《江南可采莲》说的就是这首《江南》。《宋书·乐志三》又云:“相和,汉旧歌也。丝竹更相和,执节者歌。”综合上述,可见它是汉代的民歌,本传唱于街陌里巷,后来采入了乐府,渐被之于管弦,魏晋时应还在演奏。后来的各种“采莲曲”,或与“采莲”有关的作品,如梁元帝的《采莲赋》、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、朱湘的《采莲曲》等,均发端于此诗。一直到现在,电视剧《甄嬛传》的插曲《采莲》天天盈,被唱得百转千回的,歌词仍化自此诗。
关于这首诗的诗旨,历来有很多说法,先介绍几种古代的说法。唐人是这么说的:
《江南》,古辞,盖美芳晨丽景,嬉游得时。(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二十六引唐吴《乐府古题要解》)
唐人离《江南》最近,在他们的理解中,这首诗的主题是“美芳晨丽景,嬉游得时”,即称赞美丽的自然,肯定人们的游戏玩乐切合时机,并没有荒废正事。所谓“得时”,指该玩的时候玩,该用功的时候用功。周末出游,就叫“得时”;周末补课,就不“得时”了。清人则是这么说的:
刺游荡无节,《宛丘》《东门》之旨也。(清陈沆《诗比兴笺》卷一)
“无节”和“得时”意思正相反,“无节”是没有节制,不该玩的时候也玩,平日旷了课去玩,玩的内容也比较出格。“游荡无节”和“嬉游得时”恰恰相反。此外,更有人说此诗意在“讽淫”,也就是讽刺淫荡的诗歌。清平世界,朗朗乾坤,总有道学家喜欢煞风景。
“美”与“刺”是传统中国文学批评的两个方法,“美”是赞美,“刺”是批评。对符合道德的要“美”,对不符合道德的要“刺”,美刺的标准就是道德观。无论是“美”还是“刺”,上述评论都认为此诗写的是游乐(嬉游、游荡),只不过两人对此的态度不同:唐人说玩得好,清人则说玩错了。这正是那两个时代的特色。唐代气象宽容,是妻子敢把丈夫踹掉,妻子可以改嫁的时代;清代则是要女子裹小脚的时代,是良家妇女不许出家门的时代。简简单单的两个评论,就反映了两个时代的不同。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,即认为《江南》是一首描写游乐的诗歌,对这点没有任何歧义。
到了现代天天盈,与游乐相对的“劳动”说出现了,认为这是一首“劳动诗”,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:
这是一首歌唱江南劳动人民采莲时愉快情景的民歌……本诗最主要的内容是歌唱劳动。更有人说此诗寓意在于“讽淫”“刺游荡”等等,那完全是对健康的民歌的曲解。①
在古人的理解中,“江南可采莲”就是游戏,采莲只是为了玩儿,并不是村里要创收;现代人的理解,则从“游乐”变为“劳动”,从“不健康”变为“健康”。时代真的是变了,我们进入了新社会。
二 “采莲”的演变
“江南可采莲”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,古往今来的诗人都不断地吟唱这个题材。那么,古往今来的“采莲”说的都是什么呢?我们按照文学史的脉络来看看。
南朝的梁元帝写过一首《采莲赋》,其中一段写道:
于是妖童媛女,荡舟心许;首徐回,兼传羽杯。棹将移而藻挂,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,迁延顾步;夏始春余,叶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浅笑,畏倾船而敛裾。
“妖童”是指“不正经”的男孩,“媛女”即淑女,指“正经”的女孩。“荡舟”并不是简单地划船,而是晃船,把船弄得晃晃悠悠的,如此一来,女孩就会害怕尖叫,就会抱男孩的腰,男孩的“阴谋”就得逞了。我在台湾的大学授课时,有学生告诉我,台湾男女生约会,少了机车(摩托)是不行的。男生必须有一辆机车,才可以载着女生去约会,一起看电影、逛博物馆。男生想知道女生是否喜欢他,有个测试方法,就是来个急刹车,对男生有好感的女生会抱腰,一般的就只是抓紧后座的扶手。急刹车也就是“荡舟”,“荡舟”也就是急刹车,其目的都是一样的。男孩划船,女孩采莲,男生在划船时使坏,这使坏其实就是调情。梁元帝这个做皇帝的都知道这事,估计他小时候也挺调皮的,没少“荡舟”。
南朝的版图主要在长江流域以南,像这样的采莲景象,是每年春末夏初江南的典型风景。梁元帝的《采莲赋》把“嬉游”写活了。在这里,采莲并没有“劳动”的意思,少男少女借此机会接触,最重要的就是“荡舟心许”。
过了差不多一千五百年,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写道:
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。采莲是江南的旧俗,似乎很早就有,而六朝时为盛,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。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,她们是荡着小船,唱着艳歌去的。采莲人不用说很多,还有看采莲的人。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,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。梁元帝《采莲赋》里说得好:“于是妖童媛女,荡舟心许;[插图]首徐回,兼传羽杯。棹将移而藻挂,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,迁延顾步;夏始春余,叶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浅笑,畏倾船而敛裾。”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。这真是有趣的事,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。
所谓“采莲是江南的旧俗,似乎很早就有……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”,“诗歌”指的应该就是《江南》吧?“而六朝时为盛”,大约也是从梁元帝《采莲赋》之类作品得到的印象。“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,她们是荡着小船,唱着艳歌去的”,采莲少女所唱的“艳歌”,或许也正是这首《江南》——不是有人说此诗意在“讽淫”么?《荷塘月色》里的许多描写,和梁元帝的《采莲赋》相合;“当时嬉游的光景”“一个风流的季节”“这真是有趣的事”云云,也正像是从唐吴競《乐府古题要解》的“盖美芳晨丽景,嬉游得时”而来。
有意思的是,在有些语文课本里,虽然选入了《荷塘月色》,却删去了有关《采莲赋》的那段——这与人们对《江南》的理解,从“游乐”变为“劳动”,从“不健康”变为“健康”,应该也是同步的吧?盖《荷塘月色》原本写于“旧社会”,有关《采莲赋》的那段,作者没把“采莲”理解为“劳动”,而仍旧理解为“嬉游”,甚至还遗憾于“无福消受”“妖童媛女”“采莲”的“风流”之趣,思想感情很“不健康”,自然就不该在“新社会”的语文课本里继续误人子弟了。
现代诗人朱湘也写过一首《采莲曲》,用新诗的形式写传统的题材,把“采莲”写得非常婉转优美,其主旨也同于《荷塘月色》,而与“劳动”基本无关。
无论是朱湘的《采莲曲》,还是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,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学家们,都没有把“采莲”单纯地理解为“劳动”,可能因为它们都是“旧社会”的作品。
不过,从电视剧《甄嬛传》插曲《采莲》的歌词来看,“中有双鲤鱼,相戏碧波间……莲叶深处谁家女,隔水笑抛一枝莲”,近来的流行歌曲又离开了“劳动”说,再次回归到了“嬉游”的主题;在现在的有些语文课本里,也重新恢复了《荷塘月色》中曾被删去的“不健康”段落——看来时代风气又变了。然而关于《江南》的主题,则仍保留了“健康”的“劳动”说。
❶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天天盈,北京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508-509页。
发布于:北京市天载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